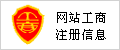那應該是2002年,水利部的官員對我說,你應該到紫坪鋪和都江堰看一看,那是四川社會經(jīng)濟以及整個中華水利文明的兩個亮點—它們相距僅9公里,時差卻足足有2256年。紫坪鋪水利樞紐是國家西部開發(fā)“十大工程”之一,四川的“一號工程”,號稱“成都三峽”;而位于其下游的都江堰則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chǎn),綿歷兩千多年“不廢不衰”,無壩分流,天人合一,是不折不扣的千古奇跡。中國歷史上兩大水利巨制在岷江上游穿越時空唇齒相依,“治水興蜀”之理想似乎水到渠成。
但紫坪鋪與都江堰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治水思想的產(chǎn)物,圍繞紫坪鋪的上馬出現(xiàn)了激烈爭論。我去紫坪鋪幾次,也寫過一些報道,在汶川大地震中,這座搖晃的超級大壩著實讓我們捏了一把汗。不過,我們暫且拋開工程優(yōu)劣利弊之爭不談,只在這兩個相距兩千多年的“亮點”之間劃一條連線,我們就會感覺到,這條連線在某種意義上暗合了中國社會組織機制的演進脈絡。
按照一些學者的說法,中國自原始社會解體之后,便進入了一種由亞細亞灌溉生產(chǎn)方式?jīng)Q定的“水利社會”,并產(chǎn)生出一整套的“治水政治”和“治水文化”。美國學者卡爾·魏特夫研究認為,中國歷史上的中央集權(quán)與大河流域生產(chǎn)關系密切相關。此說未必全對,但有助于啟發(fā)我們的思考。其實,我們自己更熟悉“治水如治國”的古訓。兩千多年來,治水對于我們從來都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戰(zhàn)略性的政治問題,帶有深刻的傳統(tǒng)文化制度烙印。我們看到了這種傳統(tǒng)社會組織模式集中國力辦大事的效力,但是—從都江堰到紫坪鋪—傳統(tǒng)水利社會的文化也面臨著現(xiàn)代社會思想的沖擊與嫁接。
“魏特夫理論”認為,水旱無常的地方往往成為人類文明的起源地,比如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中國北方、印加帝國等。在這些地方,水資源必須加以管理、開發(fā)與分配,必須興建大規(guī)模的水利工程。這就需要動員和征召人民,并需要一個強大的公共管理中心來管制足以影響國家安全的水利系統(tǒng)。當?shù)蔀橄∪辟Y源,更要仰賴中央集權(quán)管理的水利系統(tǒng),于是就會出現(xiàn)具有成熟控制體系的高度發(fā)展的水利社會。那時候,國家機器是否能夠長治久安,取決于它是否能夠有效地處理包括水旱災害在內(nèi)的社會危機,灌溉農(nóng)業(yè)系統(tǒng)的運作極大地影響到集權(quán)帝國的建立與穩(wěn)定。
據(jù)說,這種管制色彩濃厚的集體行動和公共決策一直影響到近現(xiàn)代許多國家。比如美國的田納西谷地管理局,從1930年代開始,就把中央集權(quán)與官僚化的水資源管理模式結(jié)合到流域發(fā)展計劃,以此提高落后地區(qū)的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而在1950年代,美國的另外一些州政府和全世界眾多國家都廣泛采取了這樣的水資源管理模式。
于是有人就說,從長遠看,人口在不斷增加,淡水將成為絕對的稀缺資源,只有這種官方集權(quán)式的水利行政系統(tǒng)才能有效控制與分配水資源,并使水利系統(tǒng)正常運作,進而保障國泰民安。但是且慢—由于整個人類社會的生產(chǎn)力水平已經(jīng)出現(xiàn)飛躍,經(jīng)濟、社會與生態(tài)的關系更加復雜,那種傳統(tǒng)的水利社會的生產(chǎn)關系也需要作出必要的調(diào)整,要與時俱進地調(diào)整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讓傳統(tǒng)水利社會的遺產(chǎn)更加有效地服務現(xiàn)代社會。
中國數(shù)千年的水利文明實際上是技術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結(jié)晶,都江堰工程就是一個集大成者。它留給我們的本來是一種寶貴的系統(tǒng)思想,但我們沒有發(fā)展這種思想,而是熱衷于對大項目的暴飲暴食。當我們越來越感到水資源的匱乏,往往首先向興修大型水利工程要效益,對許多問題的認知并沒有超過先輩所達到的廣度與深度。比如說,在我們的治水體系中一直缺乏法律精神與市場理念,農(nóng)耕文明的體制特征明顯,如果不能加以改進和提升,恐怕有多少水也不夠用。
在這方面,我們應該認真向以色列學習。1950年代,以色列出臺《水法》,明確國家的水資源是公共財產(chǎn)—土地可以私有,但地下水不能私有—為工農(nóng)業(yè)和生活提供用水是國家的責任,私人用水的權(quán)利取決于用水的目的是否合法。他們根據(jù)這部法律成立了由農(nóng)業(yè)部長擔任主席的水利理事會,具體制定用水供給標準—不要以為這個理事會是一個官僚集團,它的36名成員中三分之二來自公眾,只有三分之一由政府任命。在農(nóng)業(yè)部長負責實施《水法》的同時,政府另外任命一名水利總監(jiān),負責監(jiān)管國家水資源,并設立獨立的水利法庭,在水法領域構(gòu)筑了三權(quán)分立的格局,保證了決策機制和行政體系的公開、公正與公平。
在法律框架以內(nèi),以色列政府于1960年代實施配額用水制度,對農(nóng)民在配額之內(nèi)的灌溉用水免費供給,但超出配額就要高價買水。出于對生產(chǎn)成本的考慮,農(nóng)民對配額以內(nèi)的水的使用就會達到效益最大化。在這種供需機制的調(diào)節(jié)下,水資源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作為戰(zhàn)略物資的水資源的稀缺性相對減弱。以色列的經(jīng)驗說明,水資源的需求量并不必然隨經(jīng)濟成長而增加,往往是失敗的價格機制才帶來了當今水資源分配中的種種問題。世界銀行[微博]的一份報告則指出,對許多國家而言,擴增水的供給面是政治上的權(quán)宜措施,因此往往忽視了水價與需求面的管理,而單方面擴大水的供給會導致生態(tài)壓力的增加。
所以,我們在爭論治水思想的時候,不能忽略了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我們一直沒有成功的將法治和市場機制納入水資源的管理體系,這是阻礙我們進一步向現(xiàn)代社會轉(zhuǎn)型的重要因素。今后,政府對水資源管理制度的安排,以及政府自身在制度體系中的角色,將直接影響到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化進程—它們的意義要比一些重大工程更加深遠。(完)